第七章 艺术活动
1.关于“艺术”的定义
关于“艺术”的定义,美国艺术史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中描述出了这样一个相关模式。他认为,所有力求周密地给艺术下定义的人,都会涉及到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第二个要素是作品的来源,即要有一个作者——艺术家。第三个要素,一个作品总会有一个导源的主题——即它的现实起源。这第三个要素可以认为是现实中的人物、行为、思想和感情。总之可以用“世界”或“生活现实”来表示。第四个要素,就是观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
大家会发现,不论给艺术的定义如何,这些定义都会涉及到这四个要素,而各种解释、定义之间的差别,所关乎的也不过是这四个要素之间的排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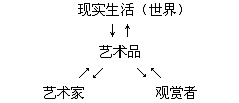
譬如,将现实生活(世界)作为作品的本源,那么艺术家的地位就会降低为次要的元素。这就是“模仿说”、“再现说”的共同特点;如果强调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那么,现实生活世界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样就形成了由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的单纯三角关系。这就是“表现说”的理论所具有的特点;如果关注的是从艺术品到读者的关系,认为艺术品应该承担教育的责任,那么,这就形成了“载道说”、“实用主义”的解释。
我们这本教材力图摆脱从任何单一元素为开端来解释艺术,而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元素看作是一个关联域,这个关联域的核心就是“存在性境域的显现活动”。
2.关于“表现说”
“表现说”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关于艺术的定义,它是随着近代以来人的主体地位的提高而形成的对艺术的观点。它是随着西方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崛起而逐渐形成的观念。
一般认为,“表现说”的观念最早的系统表述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的“序言”中提出的。在这个“序言”中,他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关于诗的主题、语言、效果、价值的系统理论。英国浪漫主义的诗人和主要批评家,几乎都是沿着艺术家→作品这条直线来讨论诗或艺术的。按照这样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艺术家本身就变成了创造艺术品的唯一本源,并且是制定艺术品的判断标准的主要因素。这样的理论就是“表现说”。
艾布拉姆斯给“表现说”所做的界定是:“表现说的主要倾向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因此,一首诗的本原和主题,是诗人心灵的属性和活动;如果以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作为诗的本质和主题,也必须先经诗人心灵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由事实而变为诗。”这样,艺术的本源也就被归之于艺术家强烈的情感和愿望寻求表现的冲动;艺术品的评判标准,也就不再是“它是否符合事实?”、“它是否忠实于自然?”,而变成了“它是否真诚?是否纯真?表达的是否是心灵的意愿、情感或真实的心境?”等。
“表现说”极大地提高了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即艺术家成了艺术作品意义的唯一来源和起源。英国诗人雪莱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诗人的听众好象为了一个听得见却看不见的音乐家的绝妙好音而颠倒的人……”。这也就是说,艺术家成了将真理带如尘世的“普罗米修斯”,是神圣的传播福音的人。与此同时,在艺术家因为这样的神圣的、意义本源的单位,他们也就被描述为天才,是审美规范和艺术标准的“立法者”。
这种思想是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关于艺术的主流思想,我们把这样的思想称作“表现主义思潮”。
3.卡夫卡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小说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1906年他在布拉格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后来一直在保险公司任职员。
卡夫卡是一个有写作愿望,但没有当作家的打算的人。他的写作也纯属“个人写作”,即他的写作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既不想给别人看,以便影响别人的生活和思想,也不想发表以便寻求社会对他的写作的普遍承认。他生前很少发表自己的作品,死后他要求他的朋友销毁所有他的文字。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也多是在自己朋友的恳求、劝说下,才发表的。
他死后,他的朋友违背了他的遗嘱,将他的全部文字整理,于1935年到1937年陆续出版了6卷集;1958年又增至9卷集。他的作品的出版,逐渐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获得了世界声誉。
卡夫卡的代表作有《变形记》、《审判》、《城堡》等。
卡夫卡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一个“异化时代”的写“异化”的作家。他的写作手法和小说的叙述手法都非常奇特,多用象征、变形和荒谬的逻辑。对这些象征、变形和荒谬,最初的感觉是不理解、不可思议,但仔细斟酌、思量,就会觉得其中韵味无穷。
应该说卡夫卡的创作,体现了艺术创作的真正本性。
4.关于“艺术品的接受”
过去的美学理论认为“艺术品的接受”,就是一个一般的赏析、鉴赏的问题。但是,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阐释学美学的影响下,德国的美学家汉斯·尧斯(1920—)和沃尔福纲·伊瑟尔等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品接受理论,被称作“接受美学”。代表性作品有尧斯的《审美经验和文学阐释学》(1967)、伊瑟尔的《隐蔽的读者》(1972)和《阅读活动——一种审美反应理论》(1976)。
尧斯和伊瑟尔都坚持认为,对艺术品的接受过程的研究,应该从作者“中心”或以作品的“原义”为中心的就理论中摆脱出来,集中到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来。他们认为,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品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的审美事实,作品仅仅是一个“召唤结构”或者“意向性结构”,只有读者的创造性参与,才能使作品的意义最终完成。在这种创造性接受的过程中,艺术品的意义的真正创造性主体不是作者,而是历史中的读者。
他们认为,在阅读活动中,读者会充分调动自己主体的能动性,激活自己的想象力、直观能力、体验和感悟力,通过对作品符号形式的了解,不但把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复现出来,而且还渗入了读者自己的人格、气质、生命意识。这样,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就不再是客观地存在于文本中的东西了,而是在创造性的阅读活动中实现出来的。
“接受美学”的理论认为,在阅读活动中,读者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一种“期待视野”中。所谓“期待视野”,就是读者在阅读中带入到阅读活动中去的预期、期待,它是由读者先行具有的“先入之见”构成的。“期待视野”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整体性预期,就是针对整个作品而产生的预期;一是微观预期,即针对每个句子、人物或情节而形成的具体预期。正是这些预期、期待激活了读者的生命,也激活了作品中的每个句子、词语、人物,使得阅读活动的整个过程变成了充满活力、冒险的过程。在阅读中,本文或者满足了一些预期,或者是一些预期落空,“期待视野”与文本具有的视野之间总会有某种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是阅读充满魅力。如果文本的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完全一致,那读者就会感到没有新意、乏味;如果文本的视野与阅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差别太大,那读者就会觉得“看不懂”。这也会影响作品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说,阅读活动中真正进行的,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视野之间的创造性融合。这也正是阅读的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