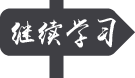知识点二:早期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印度社会的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初,已初步形成16个大国,史称列国时代,它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末、孔雀王朝兴起之时。由于早期佛教文献对于说明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性,有人称这时为“早期佛教时代”。由于当时诸邦林列而无统一国家,人们又称这一时代为“列国时代”。在政治体制上,列国中绝大多数是国王当政,也有个别国家实行贵族共和制。在列国时代后期,摩揭陀国在恒河流域中部称霸,逐渐兼并四邻,才开始走上统一北印度的道路。
列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各阶层的新思想、新宗教如雨后春笋,勃兴而发。当时婆罗门教已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和攻讦;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在思想领域中对婆罗门教的批判也导致各种新思潮新教派的产生,它们在佛教文献中被称为“外道”。
在反对婆罗门教特权过程中,耆那教占有特殊地位。传说其创始人为筏驮摩那被称为耆那大雄。耆那教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不是神创造的。世界无始无终,只有形式的变化。组成世界的万物也都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括两部分,即物质和精神两种因子。耆那教的最高理想是使灵魂脱离躯体,超越轮回,处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极乐状态。
佛教是与耆那教同时兴起的,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他成道以后所获的称号,意为“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所提倡的哲理,以及由他开始的宗教运动对东方文明影响深远。释迦牟尼是位于今天印度、尼泊尔交界处的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当他29岁时,突然离开宫廷出门修行。当时有志探讨哲理的青年人,往往采取自行流放式的修行途径。他们认为,人人都可出家,自立宗派,以求解脱,时人称为“沙门思潮”。据佛传所述,释迦牟尼追求解脱,经过长期而曲折的历程终于悟道。透悟后建立佛教,广收门徒,被门人奉为“佛陀”,意即觉悟者。由于他宣扬的佛教哲理,既博大精深,又平易近人,因而其家乡迦毗罗卫以及恒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接受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盛况超过大雄耆那教。
佛教同耆那教一样承认生业轮回之说,并认为信教修行的目的是摆脱轮回,达到涅磐之境。但它不像耆那教那样强调苦行修炼,主张进行哲理思考,了悟万物因缘,进而悟道,达于永恒的存在,这就是不生不灭的涅磐。在对待摆脱轮回的人生问题上,释迦牟尼倡“四谛”之说,从哲理角度阐述佛教所提倡的真理。四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佛教讲道的起点,也就是从人生的各种苦恼现象说起。苦谛,宣扬人生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别离、身心等八种苦。集谛,说明形成苦的各种原因,佛教避免从客观条件出发分析苦因,而专从主观方面探求。佛教认为苦的根源在于各种欲望,而各种欲望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满足。苦是以前欲望的果,果又成了以后的因,因果相袭,人生轮回不已。灭谛,说明佛教的目的是要消灭苦,佛教认为消灭苦的关键在于消除欲望。道谛,说明佛教修道的主张和途径,包括八正道:正见即信仰正;正思维即决心正;正语即言语正;正业即行为正;正命即生活正;正精进即努力正;正念即思念正;正定即精神集中,禅定正。八正道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理论上领悟佛陀所宣扬的教义,以提高信徒的宗教智慧;另一方面从静坐中体验佛陀所宣扬的境界,以提高信徒的宗教修养。
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主张“众生平等”。佛教认为神与人及众生都是平等的,社会上的不同种姓只是由于不同职业分工形成的,而不是自然如此。从这一点看,佛教显然具有积极作用。佛教的心理学学说认为,人的苦恼来源于各种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所以欲望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佛陀的伦理学强调积极精神而不是消极态度,宣扬博爱,为人服务以及助人为乐等。佛教的哲学基于唯物主义,主张除物质以外无他物,灵魂非实体。由于物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常改变形式,所以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的,只有变化的法则——生长与消灭才是永恒的。
释迦牟尼去世之时,佛教团体已初具规模,并且规定在家修行的普通信徒只要表示皈依佛法,接济僧众,并实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即可,这大大方便了佛教在群众中的流行。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佛教第一次在摩揭陀国都集结,首次写定佛教经典,此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公元前4世纪初,佛教徒举行第二次集结,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并进一步审定律藏。公元前253年,阿育王召集第三次集结,首都华氏城僧众云集,称一时之盛,主要成果是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经典的编定和佛教向国外的传播。经过这次集结,佛教经、律、论三类经典基本齐备;而佛教的远传,则表现在阿育王派名僧高士奔赴远方绝域宏扬佛法的事业上。阿育王广派传教士,东赴缅甸、南下锡兰,西达塞琉古和希腊诸国,北进克什米尔以及中亚,使佛教不仅在印度内部广为传布,且冲出国界弘扬天下,变成世界性的宗教。这第三次结集成为早期佛教达到鼎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