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鲁迅的小说创作
 知识点二:《呐喊》和《彷徨》
知识点二:《呐喊》和《彷徨》
《离婚》写出了爱姑外表的刚强泼辣,敢于反抗,但同时却也从泼辣刚强的外壳下挖掘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在小说结尾,爱姑终于屈服。鲁迅正是通过对农民,包括广大农村妇女灵魂深处的病态与弱点的开掘,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原因:近代中国在被皮走向现代化的长途过程中,最先意识到,并为这个使命流血牺牲的是知识分子。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不同阶层的沉浮过程,正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历程,而他又恰恰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他写了大量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类型(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两类:鲁迅《呐喊》、《彷徨》中有大量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鲁迅所写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有各种类型,但仍可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两类。
传统知识分子:可分为1、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写出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残废形象,封建文化只能造成历史的垃圾,没有任何生命力,只能走向坟墓。
2、被否定的反动知识分子——封建卫道士的形象:《高老夫子》和《肥皂》。《肥皂》里的四铭(虚伪的道貌岸然之徒)、《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半流氓性质的人物)。
现代知识分子:可分为1、现代社会中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药》夏瑜、《狂人日记》狂人。
2、英勇反抗旧世界、旧制度后来走向否定自己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酒楼上》吕纬甫、《孤独者》魏连殳、《伤逝》涓生、子君。
但鲁迅着力描写的,倾注了更多艺术心血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即那些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寻找道路,彷徨、苦闷与求索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具有一定现代意识,首先觉醒,然而又从前进道路上败退下来,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人物,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对于最后一类知识分子,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方面也着重揭示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在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敢于议论改革,到城隍庙去拔神像的胡子。可是一步入社会,他的改革热情便慢慢被消蚀了。为了生活,为了亲人之间的那点温情,他不得不步步退让,最终,锐气尽消,变得迂缓而颓唐,他“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靠教“子曰诗云”混日子,心安理得地干着为早夭的小弟迁葬和给一个船家女儿送剪绒花等无聊的事情。残酷的现实生活已将他的灵魂挤扁了,他无力继续为自己过去的理想而奋斗,只能凄苦地自嘲像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销磨着生命。”
《孤独者》如果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是主动妥协、自觉退让的活,那么,《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被社会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摧毁的。魏连殳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类”,最终连工作也找不到,穷困潦倒后则象孔乙己一样被周围的社会所冷落、所歧视。他不甘于这种被冷落和被歧视的地位,他要向整个社会进行报复。但这种报复也正是他的失败,他不得不屈服于周围社会的价值观念,采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向社会进行着盲目的报复,甚至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起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伤逝》中的子君、涓生追求的目标要比魏连殳小得多,他们只是希望获得婚姻的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共同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但整个社会的陈滞、腐朽却不可能不毁灭掉这个爱情的绿洲。中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中国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结成的“神圣同盟”),社会过于黑暗,在广大的社会群众实现广泛的思想启蒙和广泛的社会解放之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要单独地实现他们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但作品对其主观原因的揭示同样是深刻的:这对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由于他们把争取恋爱自由看作是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缺乏更高远的社会理想来支撑他们的新生活,因而使他们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结果,子君只好又回到顽固的父亲身边,最后凄惨地死去,而涓生则怀着矛盾、悔恨的心情,去寻找“新的生活”。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与道路的主题,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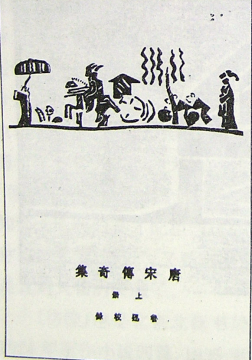
鲁迅《唐宋传奇集》封面
B、独特的眼光(观察视角):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
1、农民题材的视角:在《药》里,鲁迅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样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
2、知识分子题材的视角:也是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在酒楼上》中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吕维甫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甚至进而变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的。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 的小说的现代性的。
C、小说模式:常见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 与“离去——归来——再离去”。
1、看/被看:《彷徨》里有一篇颇为独特的小说:《示众》。小说没有一般小说都会有的情节(故事)、人物刻画和景物描写,也没有主观抒情与议论,只有一个场面:看犯人。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叫卖馒头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还是有着发亮的秃头的“老头子”,梳着喜雀尾巴似的“苏州俏”的“老妈子”,“一个猫脸的人”,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 /被看”的二元对立。小说不着意刻画人物或描写,而主要写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情节,这反而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内含着多方面的生长点,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里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从而构成一个系列。如《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药》、《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等。
“看/被看”的二元对立不仅发生在庸众之间(《示众》)也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的对象活活地吃掉;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药》)、孤寂(《孤独者》),以致恐怖(《狂人日记》)、愤激(《头发的故事》)与复仇(《孤独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届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2、“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是《祝福》、《故乡》,还是《在酒楼上》、《孤独者》,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象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还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圆圈)。
《祝福》里其实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与“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