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30年代小说
 知识点二:左翼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
知识点二:左翼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
③ 艺术特色
穆时英的小说,可以说是现代的“有意味的形式”,沈从文说他“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所谓的“穆时英笔调”、“穆时英作风”在当时风靡上海滩,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穆时英的小说不但具有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又随时能够做激烈的动作描写,讲究节奏、快速组接,特别富于刺激,因此有人说他是技巧派。
穆时英的小说在总体上呈批判性,如《上海的狐步舞》,全篇表达的就是“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旨意。但是对于一个个的局部,如舞厅、夜总会、饭店等,又呈现出迷醉的状态。
刘呐鸥和穆时英,虽然是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新感觉派作家,但是从个人品性来看,却是利欲熏心的无聊文人,因为长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其小说虽然客观上有揭示社会黑暗的意义,却往往没有正常的道德评价和善恶的判断,充满着对感官刺激和肉欲享受的欣赏和玩味,以及对自我暴露和自我本能发泄的满足。这样的一种贪图个人享乐、漠视社会苦难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卖身投靠,成为了汉奸,1939年,在沦陷区的上海,两人一起担任了汉奸政府创办的《中华日报》的编辑,并先后出任《文汇报》社长等职,但是投靠汪伪政权不久,就于1940年先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杀害。
(3)施蛰存(1905-20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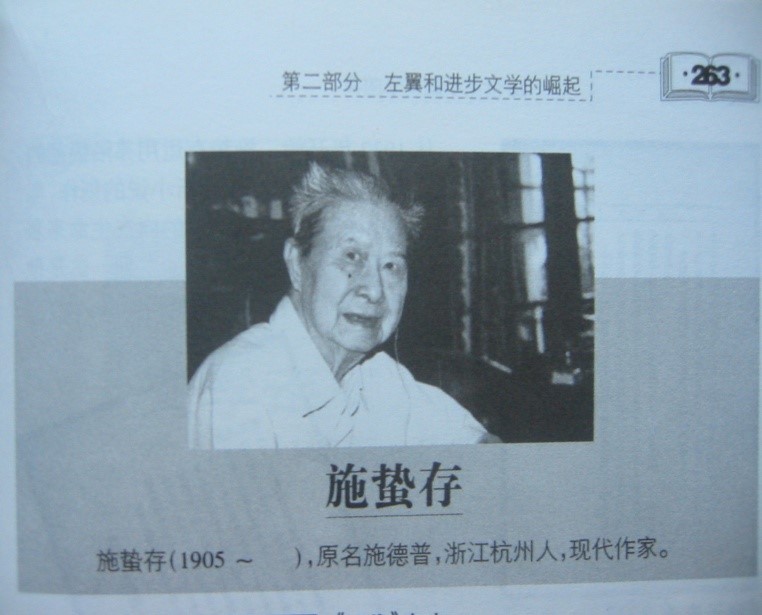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施蛰存
① 小说创作及文学史地位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其中比较特异的人物。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人相比,施蛰存的小说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多样。
施蛰存的第一个短篇集是《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了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杂志后,开始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地合流。代表作是《梅雨之夕》、《春阳》、《善女人的品行》、《将军底头》等。
② 心理分析小说
施蛰存更擅长描写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特别注重挖掘都市市民的深层心理世界。这种倾向最终发展为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梅雨之夕》和《春阳》都揭示了都市男女隐秘而曲折的内心流程,写他们卑微的渴望的萌动和这种渴望的无声无息的破灭,力图展现现代都市男女特有的情爱方式。
《梅雨之夕》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文章的题目“梅雨之夕”暗示的是男主人公情感的现实处境。故事中的绅士“我”在下班的路上,适逢天下起了雨,并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退到屋檐之下去避雨,受潜意识的驱动,他也退到了屋檐下,内心深处经历了 “过去还是不过去”的剧烈的情感挣扎后,最终某种被压抑的情愫占了上风,他举起伞,将那个姑娘邀到了伞下,并送其回家。接着作家用精微细致的笔触描绘他一连串的散文似的艺术流动:一会儿觉着这个姑娘是自己的初恋情人,一会儿觉着自己的妻子在近处盯着,一会儿害怕在路上碰着熟人,等到把姑娘送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又觉着自己妻子的声音也象那个姑娘的声音。他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象是不可理喻,实际上是他的潜意识在作祟,所有的不可理喻都是因为一个理由:对真实的爱情的向往。绅士在雨中遇到的少女是其情感上梦寐以求的伴侣,而雨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不可以诉诸于理性的,所以他一回到家,梦立刻就醒了过来,向妻子撒了一个谎后,一切自然的真实的情感和性意识又重新被压抑了起来。这种情感的来或去,都不是刻意的,事先没有丝毫的征兆,潜在的意识和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一切,同时又毁灭了一切。
《春阳》中的婵阿姨年轻时为了钱同丈夫的牌位拜堂,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对情欲的渴望却仍然留在心底。作品从她某天来到上海银行取钱写起,通过她在春天暖阳的照耀下萌发的对一个年轻银行职员的爱欲冲动,表现了人性无法压抑的思想,对封建道德摧残人性,对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异化人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小说采用的也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将军底头》和《石秀》等小说,用心理分析的手法重新演绎了古代题材。《将军底头》重点展现的是唐代将军花惊定处在情欲和种族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挣扎的痛苦,带有一定的神怪和魔幻色彩;《石秀》揭示的则是友谊和色欲的冲突。《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石秀,在施蛰存的笔下成了一个色情狂和性变态者,在友谊与色欲中煎熬的悲剧人物。
③施蛰存小说的艺术特点:
首先,通过潜意识探索人性,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核心追求;其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又一特点。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比,施蛰存的小说有着同样鲜明的现代艺术,但是叙事的技巧相对传统些,节奏比较平缓,故事性较强,有一种怀旧的气息和古典的诗情。这和他小说的都市图景后面的乡土背景有关。施蛰存虽然住在上海,但是在松江还有故居,这是他的文学后院,从而缓解了都市的忧虑感和孤独感。
施蛰存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是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且付诸了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的影响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是比较公允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