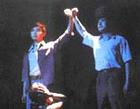中国当代戏剧发展概况(1949——迄今)
新时期话剧:
80年代的戏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7—1979年是第一阶段,戏剧从一片废墟上再生,现实主义戏剧传统恢复井取得了重要的收获;1980—1985年是第二阶段,“话剧热”突然降温,戏剧工作者在危机中借鉴西方现代据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革新,戏剧观讨论引起理论热,留下了一批探索戏剧;1986—1989年是第三阶段,在总结探索戏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戏剧工作者进行着更为坚韧的探索。此时小剧场运动引人注目。
1977年是新时期戏剧孕育、再生的一年。首先是重新上演部分优秀剧目,同时,戏剧界展开了对于“四人帮”“阴谋戏剧”的批判。在重演和批判中,新时期的戏剧得以孕育和再生。《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曙光》的问世,标志着话剧创作的再生。《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编剧,1977年)是一出政治喜剧,以辛辣的讽刺剥开了“四人帮”政治欺骗的画皮。
 《枫叶红了的时候》剧照
《枫叶红了的时候》剧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家思想进一步解放,剧作界因之出现了短暂的百花争艳的局面。与最初两年有重大影响的剧作产生于京、沪两地的局面不同,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东北、西北、中南、华东都出现了具有影响的剧目。从主题、题材看,虽然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作品仍然是创作的主流,如《有这样一个小院》(李龙云编剧,1979年)、《神州风雷》(赵寰、金敬迈编剧,1979年)、《左邻右舍》(苏叔阳编剧,1980年)、《九一三事件》(丁一三编剧,1981年)等表现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及其爪牙斗争的剧作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是更具时代特征的是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时期现实生活的作品,一些作品接触了现实社会生活中重大矛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了解放思想、面对现实的特点。《报春花》(崔德志编剧,1978年)、《未来在召唤》(赵梓雄编剧,1979年)、《救救她》(赵国庆编剧,1979年)、《权与法》(邢益勋编剧,1979年)、《灰色王国的黎明》(中英杰编剧,1980年)等剧都曾因其及时地提出社会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出身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失足青年问题、权太子法的问题、封建残余的问题等等),而引起极大反响。这些剧作的向世,标志着80年代现实主义戏剧鼎盛期的到来。一些冲破禁区的作品相继上演,比如《爱情之歌》、《原子与爱情》之写爱情,《闯江湖》(吴祖光编剧,1979年)之表现旧艺人人生,《泪血樱花》、《鉴真东渡》之搬演中日关系的故事,《大风歌》(陈白尘编剧,1979年)、《王昭君》(曹禺编剧,1979年)之反映历史人物,乃至上演翻译的布莱希特名剧《伽利略传》等,突破了题材禁区,为丰富戏剧舞台做出了贡献。在艺术上,人物形象的塑造自觉清除“高大全”、“三突出”模式的影响,致力塑造有血有内的舞台形象,创造出了梁言明(《未来在召唤》)、李健、白洁(《报春花》)、方凌轩、丁文忠(《丹心谱》)等较为感人的艺术形象。老一辈革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转折》(周来、王冰、林克欢、赵云声编剧,1977年)、《报童》(朱漪、邵冲飞、王正、林克欢编剧,1978年)中领袖形象还只偶一露面,《曙光》、《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姚云焕、胡耀华、黄景渊编剧,1978年)、《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1979年)、《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1980年)、《转战陕北》(马融编剧,1980年)、《彭大将军》(王德英、靳洪编剧,1981年)等剧作中,贺龙、周恩来、陈毅、彭伯怀、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已成为剧作的中心形象,《
陈毅市长》等作品中,领袖人物已经从理想化、神化、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逐渐走向“人化”。不过,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戏剧观念和艺术手法等方面,这些作品基本承接了“十七年”话剧模式,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
进入80年代,“话剧热”降温,话剧开始步人困境。导致降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话剧生存的社会环境变化的原因,也与经济生活日益成为关注的中心,中外交流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大规模开放,休闲方式的多样化等因素有关,而话剧自身诸如创、演体制问题.戏剧艺术从观念到形式方面的单一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困境激发了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艺术的探索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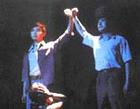 《绝对信号》剧照
《绝对信号》剧照
与戏剧理论的探索同步进行的是剧作界的创作和舞台实践的探索。最早引起社会关注的探索戏剧是哲理剧《屋外有热流》(独幕剧,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编剧,1980年4月上演,载《剧本》1980年第6期)。至1984年、1985年,戏剧探索的浪潮达到波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西方现代戏剧观念和手法影响着探索戏剧的进程。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1981年:《血,总是热的》(宗福先编剧)、《秦王李世民》(颜海平编剧)、《阿Q正传》(陈白尘编剧)、《路》(马中骏、贾鸿源编剧),1982年:《
绝对信号》(高行健、刘培公编剧),1983年:《车站》(高行健编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刘树纲编剧)、《生命?爱情?自由》(罗国贤编剧),1984年:《周郎拜帅》(王培公编剧)、健小巷深深》(王树元编剧)、《本报星期四第四版》(王承刚编剧),1985年:《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编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马中骏、秦培春编剧)、《天边有群男子汉》(周振天编剧)、《野人》(高行健编剧)、《魔方》(陶骏编剧)、《WM(我们)》(王培公编剧)等。
1985年底1986年初,波及全国的喧嚣的探索戏剧热开始消退,此后,在日趋平静的探索剧坛上留下的就只是坚韧者的足迹。这一阶段,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吸收、消化西方现代派戏剧美学的形态出现。《黑骏马》(罗剑川编剧,1986年)、《
狗儿爷涅槃》(刘锦云编剧,1986年)、《寻找男子汉》沙叶新编剧,1986年)、《洒满月光的荒原》(李龙云编剧,1987年)、《中国梦》(孙惠柱、费春放编剧,1987年)、《二十岁的春天》(余云、唐颖编剧1987年)、《桑树坪纪事》、《芸香》(徐频莉编剧,1989年)、《蛾》(车连宾编剧,1990年)等剧作,显示了话剧探索的深化。
 话剧《狗儿爷涅槃》剧照
话剧《狗儿爷涅槃》剧照
80年代戏剧,值得关注的还有
小剧场运动。欧美小剧场运动已有百年历史,20年代“爱美剧”是小剧场运动在中国的初次实践,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绝对信号》,标志着小剧场运动的复兴。此后,在1982年至1987年间先后有上海青年话剧团、哈尔滨话剧院、广东省话剧院、南京市话剧团、大连市话剧团、沈阳话剧团进行了小剧场戏剧演出的实验。1988年是小剧场话剧的丰收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青艺小剧场”改建成,并上演《火神与秋女》、《天狼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了《女人》,南京市话剧团在连续上演几部小剧场戏之后,又上演了新作《天上飞的鸭子》。1989年4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南京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9个话剧院、团上演了16个剧目,显示了小剧场戏剧的实力。
 话剧《留守女士》海报
话剧《留守女士》海报
1993年北京有“‘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其中《留守女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尼姑思凡》(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情感操练》(火狐狸剧社演出)、《泥巴人》(广东省话剧院、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两台演出)受到好评。戏剧工作者试图建构起与当代普通观众的欣赏要求相沟通的桥梁,把视点逐渐转向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与感情表达,为赢得观众而进行通俗化追求,从不同角度探求小剧场创作的潜能。这次展演显示出部分戏剧工作者探求戏剧生存之路而进行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