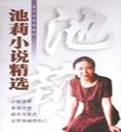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所谓“后新时期”之说,虽然至今“后新时期”的内涵还是众说纷纭,但其所标示的90年代和80年代文学的差异则是明显的。90年代的商业文化语境使得中国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文学的边缘化恰恰使90年代成了一个真正自由、自主的文学时代、一个真正反映个性特征的文学时代和真正多样发展的文学时代。90年代的文学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实现一种真正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严肃与游戏、创新与守旧、通俗与先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都有相应的文学表现。这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被大幅度地拓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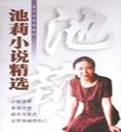 《池莉小说精选》
《池莉小说精选》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
9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崛起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等中短篇小说及近期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和范小青的《百日阳光》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都以其特殊的当下品格而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评论界称他们的创作是对新写实小说的全面超越,是“现实主义的大潮再起”,是“主旋律”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与新写实小说相比,他们的创作仍有着对于人的生存本质的勘探、对于个体生存困境的表现的特色,但他们小说的当下性特征和情感性特征显然得到了强化,艺术表现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为90年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对于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女性写作的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独特的内涵,并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推动曾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在90年代女性作家的多元构成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那些穿越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在90年代的风采依旧和初显大家风范,也可谓是90年代女性写作渐入佳境的一个重要标志。
90年代王安忆的创作更是在对世界感受的深度上、在对小说叙事现代性的探索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迟子建在90年代也一度呈现出劲健之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叙事老练、流畅,对世界和世道人心的把握举重若轻。只可惜,她的这种势头没有能很好地保持下去。此外,池莉、铁凝是另两位保持着80年代小说创作的良好势头的作家。
构成90年代女性写作另一极的,是90年代崛起成名的女作家群。她们是陈染、林白、徐小斌、斯妤、徐坤、海男、张欣、毕淑敏、张梅等。这些作家体现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这也是如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遭非议最多的一脉。对于陈染来说,她的笔所指向的完全是女性个体独特的经验世界。她用女性个人的体验方式来命名自我和存在。从《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等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她都以一种近乎呓语式的内心独白体对女性的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陈染不仅以她哲学化的生存之思向读者敞开了女性世界的神秘,而且还以她特殊的语言方式、感受,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二是以徐坤、斯妤为代表的解构性女性写作倾向。这类作品也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但作家的表现方式却不同于陈染、林白式对于女性经验的敞开、珍视和渲染,而是暂时忽略和放弃对于女性躯体的热情,直接以对于男性世界和男权文化秩序的怀疑、解构为艺术目标,以曲线方式张扬女性主义。徐坤在90年代曾被戏称为“女王朔”。她的《白话》、《斯人》、《狗日的足球》、《厨房》都以一种特有的调侃、反讽的方式对男性世界实施着无情的解构。
 《毕飞宇小说》
《毕飞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