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鲁迅的小说创作
 知识点二:《呐喊》和《彷徨》
知识点二:《呐喊》和《彷徨》
三、《呐喊》、《彷徨》小说集杰出的艺术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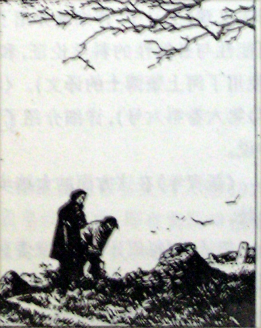
鲁迅小说《药》的木刻版画
包括《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在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高峰。“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纵观《呐喊》和《彷徨》,它们无论在其思想性还是在其艺术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把握鲁迅小说的高度成就,可以用鲁迅自己的两句话: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前一句指独特的题材与思想发现,后一句指小说结构模式与形式手法的创新。
(一)“表现的深切”一—独特的题材、眼光(视角)与小说模式。
A、题材方面: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
鲁迅在论及中国文学的变革时,首先提到的是文学题材、主要表现对象的变化。他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鲁迅创作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所以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由此开掘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类题材。
鲁迅小说劳动人民(农民)主题的重大意义:文学史上写作对象的转变:世界文学由“神(古希腊神话)——半人半神(《荷马史诗》)——人——下层人”18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出现后文学描写对象转向人如斯丹达《红与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出现后,文学开始大量描写下层人民形象,如左拉、狄更斯等。中国文学的描写对象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完成描写人物向下层人民转变的工作这是鲁迅小说的历史意义。
鲁迅表现劳动人民(农民、妇女)有以下特点:1、对下层劳动人民深重苦难的真挚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2、沉痛揭示和批判下层人民的精神弱点,提出和表现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主题。下面我们详细讲解:
1、农民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在《呐喊》、《彷徨》中,农民题材的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深切同情的,他看到农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当然也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在创作中,鲁迅一方面把中国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心理和意识结构等)中加以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革命、变革和社会震荡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鲁迅着力塑造在这一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在这方面,《阿Q正传》堪称代表,其他如《药》、《风波》、《故乡》等也是如此。
《药》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的故事,真实地显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由于这场革命没有真正唤起民众,因而缺少群众基础,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华老栓们的无知、迷信,既是落后、愚昧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
《风波》的背景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期江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小说通过发生在 乡场上的一场因“皇帝又要坐龙廷”而引起的复辟与剪辫的风波,揭露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停滞、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愚昧与精神麻木。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夜,华老栓父子对夏瑜的鲜血的亵渎,是出于愚昧而对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冷漠无知,也是革命本身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的暴露;那么,许多年之后,七斤一家在赵七爷的“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威慑下所流露的惶恐、昏乱与茫然,则是从更深刻的历史层次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实际结果:中国封建社会 的旧基础并没被摧毁,由这个旧基础培育出来并维护这个旧基础的封建意识形 态和落后愚昧的精神并没有被消灭。

小说《故乡》插图
《故乡》中,辛亥革命后的农村,却愈益萧条,淳朴的农民们仍然生活在困苦之中。作品最震动人心的还不仅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一声“老爷”中所显示的精神的麻木,以及在无出路之中把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烛台的迷信和愚昧。
鲁迅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农村现状和农民的生活图景,在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联系中探索农民问题,这里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思想认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以农民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影响。
2、妇女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在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的一组以反映农村妇女 命运为内容的作品,如《明天》、《祝福》、《离婚》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在感受着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的精神苦痛,把批判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的同时,更集中地对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清醒的批判。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重要的是她周围一般人对于受苦人的冷漠以及她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得不承受的精神上的孤独和空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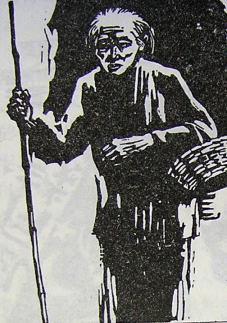
《祝福》插图
《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批判了造成其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编织成的严密的网;另一方面,作品也把谴责的笔指向了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婆婆的凶残、短工的麻木、堂伯收屋、鲁镇群众的奚落、柳妈告之以死的恐怖,他们和祥林嫂同属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又是他们维护着“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折磨着祥林嫂,不仅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构成了她悲剧的一个原因。作品深刻之处在于,写出了祥林嫂的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还在于她自身的原因:她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她的出逃、抗婚等反叛行为的背后却是“从一而终”的封建“女德”,她的捐门槛是出自在封建神权下感到的精神恐怖,一句话,她以封建礼教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