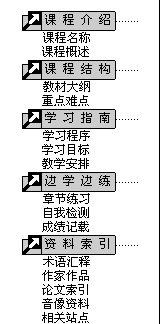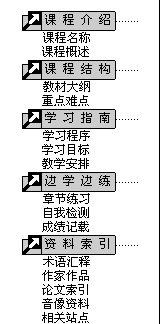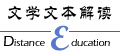叙事视点
一、叙事视点的涵义
所谓"叙事视点",也成叙事视角、叙事角度、叙事观点,指的是作家安排组织故事内容的角度,也就是一个"谁"站在什么"位置"来讲故事的问题。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叙述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作家政事根据他所选择的叙事视点将故事--事件、人物及相关的一切--告诉我们的。不同的叙事视点,也必然会影响到所叙内容的"质量",比如真的还是假的?是事情的全部或仅仅只是事情的一个极小部分?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小说的阅读者,小说的叙事视点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从故事的叙述中能够看到什么和应该怎么去看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小说讲述的故事,特别是故事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所做的反应。也就是说,小说的叙事视点的确定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故事叙述的方便,更重要的,它还体现着小说家希望读者看到什么,或者这种表述取得何种文体上的效果的主观意图。叙事视点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因而,关于视角也是众说纷纭,名目繁多。这里,我们分为全知视角叙事、限制视角叙事、纯客观叙事。
二、全知视点
所谓"全知视点"是指作者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威,作者能够洞察秋毫,把事件和人物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出来,极富有立体感。很多世界名著都是运用的在这种叙述视点,中国古代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作者凌驾与小说世界之上,居高临下,洞察一切,调度一切,用穿透一切的"火眼金睛"去观察世界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观察人物的言谈举止,内心活动。他了解人物的一切,甚至是人物自己根本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可以一会儿进入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会儿又说说那个人物的潜意识;一会儿说说这个人物的隐私,一会儿又讲讲那个人物的往事。他既可以象一个隐形人一样任意出没于故事的任何一个角落,也可以跳出小说世界,亮出作者的权威身份,发表自己的感想、见解和评论。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陈小手》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过去时代乡村男性妇产科医生陈小手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极其平淡,就好象茶余饭后,乡亲们搬出凉椅在院子乘凉,有位见多识广的老乡给大家在讲叙一件见闻。紧接着,小说又给我们很细致地介绍了"我们那个地方"生孩子的乡俗、陈小手作为一个男性产科医生的特别、陈小手在"我们那个地方"的声誉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随着故事的讲述,来到了陈小手一生中最后一次展示他高超助产技术的那个时刻。故事讲的很细致,很清晰,也很平易,没有一丝的板滞。从小说开头"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小说也就是以知情人的身份和语气讲述,也就是"全知视角"。由于采用的是"全知视角",所以讲述者什么都知道。讲述者站在一个高于故事中任何一个人物的角度,俯瞰全局,每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他都尽收眼底。因而他可以知道陈小手的一切,包括他杰出的医术、他在产房里的活动;知道产妇临产时的痛苦,以及产妇在痛苦中听到陈小手的白马脖子上銮铃的声音一下子就会心里安定起来的情形;知道团长女人的肥胖;知道团长的委屈……
选择某一种叙事视角并非任意为之,而是为了达到某种作者期待的叙事效果。《陈小手》就是如此。这篇小说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而讲述者的任务就是原原本本地交代清楚故事的一切,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全知视角"恰倒好处地适应了作者的这一要求--不承担讲故事以外的任何任务。读过故事之后,我们的感觉还真是如此,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完完全全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作者对陈小手的赞叹,不知道作者对陈小手无辜冤死的惋惜,不知道作者对杀人团长的指责,总之,我们从故事中看不到作者对任何一个人物的明确的态度,作者总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讲述着,他的倾向只会从情节和场景中自然而然地流露。这样,给读者就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使得讲述本身充满耐人回味的魅力。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鲁迅的《示众》、《肥皂》等也都是采用的这种"全知视角"。
三、限制视角
限制视角,又称次知视角。作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叙事,只展现事件和人物的一部分,而不展现全部。所以,又称为局部化叙事。当作者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叙事时,大多是限制视角,于是,又有角色叙事的说法。充当叙事者的人物对自己来说是全知的,对别的人物来说就是限制的。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可以解剖自己的一切,却不能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作品只有这一个人物可以从内部来写,作者仿佛坐在这个人物的大脑里,观察其他的人物和事件,所以,其他的人物和事件都只是从外部观察得来的结果。充当叙事者的人物可以是主要人物也可以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限制视角叙事可以避免全知视角叙事的冒险。当作者对所叙之事不完全清楚时,他可以采用限制视角,只说知道的,回避不知道的部分。作者还可以用限制视角从各方面拉开和故事的距离,他甚至可以用选用一个愚蠢的人,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与自己观念相反的人物充当叙事人,以他们的眼光去看世界。
鲁迅的《祝福》就是使用的这种限制视角。"我"知晓祥林嫂的故事,却不知道她的内心的苦楚;我看到了她的孤立无助,去看不到她的潜藏的悲哀;我听到了他人对祥林嫂的鄙视与不屑,去听不到她的呐喊和申诉。我只能讲述我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我无权对祥林嫂的内心世界进行解剖,我只能从她的言行举止中推测她的想法。透过"我"的视线,我们看到了一个颇令人同情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她没有自我,被自己的婆家欺负,被镇上的人鄙视,四处孤立无援。她原指望从"我"这个读书人处求得一点指点,可也是失望而归。限制视角使我们不仅认识了祥林嫂,也认识了"我"。"我"对于祥林嫂是同情的,可"我"又仅仅止于同情,未能给她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我"对自己不断地反省,正是在这反省中,祥林嫂的形象渐渐立了起来。我们在阅读中会既被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所打动,也会因"我"对自己内心的审问而深深思考祥林嫂的悲剧究竟来自何处?因此,小说的阅读感受就此丰富和复杂起来。鲁迅的许多小说都采用的是这种"限制视角",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鲁迅的深沉的叙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