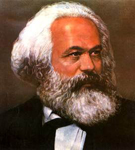| 上一节 | 下一节 |
|
第四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关于史学,马克思关注的重点在于历史哲学的层面。他的历史思想谈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模式、动力和规律,以及何为历史主体,何为理想的社会形态等一些列宏观的、本原性的问题,而不是去关心历史编撰的具体类型或考证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 马克思的历史观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但它的思想全面反映了19世纪历史学的成就,也是至今依然具有影响力的历史观之一。由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以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通常习惯成他的历史细想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同其他的系统理论一样,其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必然的社会基点、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 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处于一种宗教和君主并存,政治统治权难于固定的状态,至各国陆续进行工业革命后,大量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加入到了各国政治统治集团当中。封建君主们刚刚去除了凌驾于他们头上的教会的制约,又发现资产阶级已经试图在政治上与他们分庭抗礼。而资产阶级自从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成为社会经济新的主角之后,一方面无法割舍与旧的封建集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不堪忍受政治无权、经济垄断的尴尬处境。社会的统治阶级无法达成一致,加重了广大的平民百姓生活得负担。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前夕,伴随着政治改革的走马换将,欧洲各国的革命也接连不断。但这种革命多是一时义愤和无序的暴起,根本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从理论的层面很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尝试着找到一种可以更直接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指导性理论。可见,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唯物史观不仅仅像其他人的社会学理论那样,直面社会问题而缺少扎实的理论支撑,相反,他的思想在触摸着时代跳动的脉搏同时,又合理的借鉴了前人伟大的理论成果。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重视人本身,到强调理性、真理和自由的漫长过程。从“重视人”到“重视所有人”,西方人对于生命价值和幸福的看法与标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西方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却往往不是西方学者所关注并习惯于与精神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学者认为,文艺复兴的出现是由于人对于自我价值和自身欲望的释放,因此它是真实的,而由于它缺乏高尚的道德和思想的约束和指引,却又是堕落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渴望用理性去塑造一个理想社会,虽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却失败于现实的残酷。历史哲学家往往试图探明人类历史,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动力和规律,但却无法利用精深的理论改变愈发混乱的近代欧洲。在理性主义史学家看来,只要运用理性,便可以改造社会,拯救黎民,实现永恒的正义与真理,建立有利于一切时代与民族的社会制度。依据这种被夸大了的理性,史学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史学实践,也未能找到真正的理性王国。并且,理性主义史家原本想借助理性科学的力量,沿着人文主义史家的足迹,继续驱逐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史学中的“神圣的天意的干预和教皇的活动”, 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基督教思想和神学思想的坚持性和潜在力量”。 深刻的理论与残酷的现实脱节、伟大的思想对广大民众的忽视,成为了欧洲各国无法解决社会混乱的症结所在。马克思睿智的审时度势,找到了这一矛盾的根本所在。他避开了形而上的空想与模式化的理性纠缠,另辟蹊径,以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借鉴了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合理内核。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唯物史观,为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 19世纪自然利学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有组织、成体系的整体。它关注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热心于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宏大的、整体的、联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及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这样,自然界也被认定为,是一个动力不变,基本单元一定,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观念影响到了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样也影响到了历史学。受到自然科学影响的,首先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批学者。 把人类社会比喻为“有机体”的思考自古就有,但是比较专门而有价值的探讨则始于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特别是英国的斯宾塞。圣西门初步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的学生们则明确提到“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并要求分析社会这个统一整体的“各个器官”。作为圣西门秘书的孔德把社会与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论”作比较,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种族或阶级是社会的组织,社区或城市是社会的器官。后来,英国的斯宾塞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的同与异作了比较分析,他认为,社会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有机体,而是一种“超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并完全从属于整体,社会超有机体的各部分的活动比较分散与自由,因而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整体,但又是一个可自我调节的系统。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并不是区别于自然界的特有组织,而同样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一个重要来源。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史家爱尔维修看到了社会环境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著名命题。这一命题为历史研究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即历史研究不应从人们的观念、思想中左寻找历史原因,而应到社会环境中去寻求。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使19世纪复辟时期的史家认识到阶级形式在社会中的存在。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认为“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这就提供了历史分析的新元素。 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黑格尔力图证明历史发展并非杂乱无序的偶然事件,这在马克思以前,是第一个企图在历史观中使用辩证法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的人。他不仅把社会更替看成是一个合乎理性规则的过程,而且还把世界历史看成是各民族相互联系和不断进步的辩证过程。 |